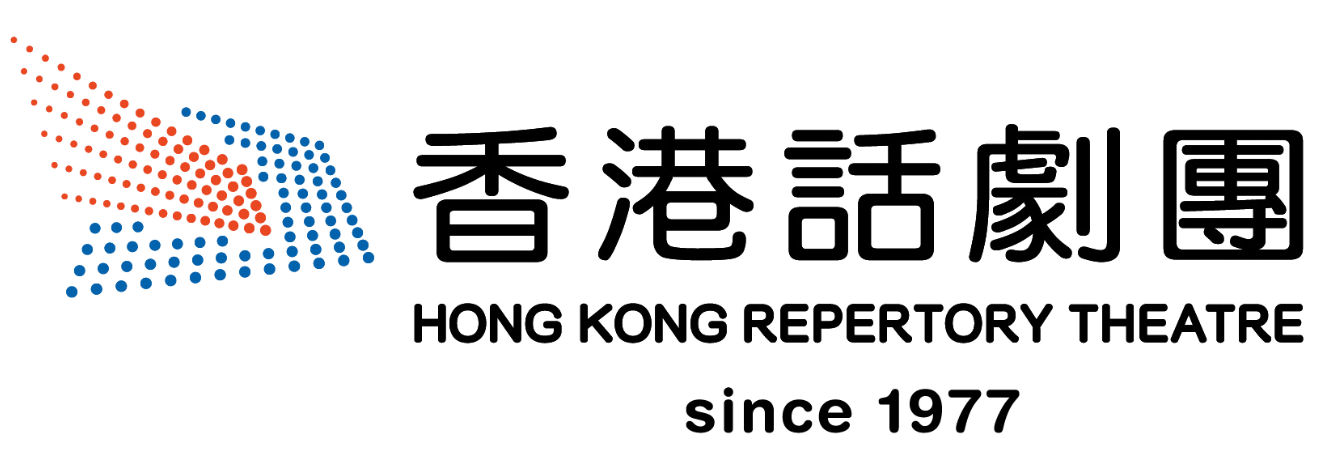戲劇文學
武松的退隱與執念
1.
《水滸傳》的主題之一是「退」。
在整部《水滸傳》裡,沒有一個字解釋過何謂「水滸」。「水滸」一詞其實出自《詩經》,在《大雅‧緜》中有言:「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水滸,即河水之邊,全句說的是一個典故:周朝的始祖亶父牽著馬匹,率族人來到西水之邊,最後到達岐下這個地方。要知道,當時為商代,按《小雅‧北山》更廣為人知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天下盡是商天子的王土,那麼亶父只好遠走西陲之地,才能擺脫天子的掣肘。於是「水滸」便有如下引伸意思:不受朝廷控制的淵藪地。
《水滸傳》講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打家劫舍、對抗朝廷,好不熱鬧。然而全書一百二十回,真正齊集眾人的篇幅其實不長,從七十一回梁山好漢排座次,到八十二回宋江接受招安,前後只佔不到十分之一。素來讀者多不喜招安後的故事,招安後,梁山泊好漢替朝廷賣命,最後落得死傷枕藉的下場,令人唏噓。而招安一節更常被斥為投降主義,此批評即使與政治無關,其情也滿不是味兒。所以水滸故事中,前七十回流傳最廣,當中又有一種情節特別醒目:一個武藝不凡、急公好義的好漢,因犯官非而鋃鐺入獄、刺配邊疆甚至有被問斬之虞,走投無路,最後只好落草為寇。
因此,「梁山」往往不是好漢們的人生目標,而是體制容不下他們,他們無處可逃,只好逃出王土,走馬至水滸,「逼」上梁山。有人認為,施耐庵寫宋江接受招安,是情非得已,卻也是情理之內。梁山泊終非久安之地,這樣巨大的一個軍事集團,宋江身為領䄂,也得為一眾兄弟謀求出路。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接受招安。梁山好漢中,有不少本來就是朝廷的高級軍官,像林沖,風麈味本就不強,只因朝廷腐敗,或得罪權貴,逼不得已才落草梁山,招安反而是一個平反機會,正是求之不得。但另一部分人本來就是混跡江湖,或是販夫走卒、低級衙役。他們都是體制內的弱勢族群,退上梁山雖是為勢所逼,卻也逍遙自在。這批好漢對招安一事最不以為然,只因他們向來自由,不甘吃體制一套,做慣山賊自然懶做官。
宋江本是體制裡的低級官吏,卻有建功立業之志。他在潯陽樓牆上所題反詩:「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正顯露了心跡,他的哥兒們卻沒有此等豪氣。《水滸傳》中有兩個要角跟宋江特別親近,一是武松,一是李逵,兩人跟宋江相識甚早,受過宋江的義氣恩情,故對他馬首是瞻。可是兩人卻十分反對宋江接受招安。李逵粗豪魯莾,一心想著殺入京城,擁護宋江哥哥做皇帝,大伙兒都做大將軍。但他思想單純,敬重宋江,最後還是受宋江制約。武松比李逵沉著、世故,他雖然反對招安,最後替朝廷平亂時還是出了不少力。
武松跟李逵的結局是令人唏噓的。自古朝廷不可靠,鳥盡弓藏是常態。宋江替朝廷平定內亂後,高俅以毒酒毒殺宋江,宋江死前生怕李逵會在自己死後作亂,故要李逵也喝一口毒酒,與他同死。李逵居然對此無怨無懟,還道:「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的一個小鬼。」至於武松,他在戰爭中失了一臂而成殘廢,戰後亦無顏面回朝接受封賞,便在五台山出家為僧,反避過兔死狗烹的一劫。
所以《水滸傳》是一個關於「退」的故事。李逵和宋江就是因沒有「退」而命喪九泉的範例,而武松,則是一個「退」的例子。
2.
潘惠森多次改寫《水滸傳》,鍾情的還是宋江、李逵和武松的三角關係。1990年代,他已寫過《武松打蚊》、《李逵的藍與黑》和《宋江採花》三部改編自水滸的劇作,《武松日記》雖可說是《武松打蚊》的創作延伸,卻處處顯露出與其餘兩個劇本的文本互涉關係。《武松日記》原是小說,在2001年《武松打蚊》重演時,潘惠森於網絡上同步發表這部小說體外傳(潘惠森本人戲稱為「偽小說」,後收錄於《男人之虎─ 潘惠森喪無聊偽小說集》),小說情節跟《武松打蚊》無直接關係,卻呼應了《李逵的藍與黑》和《宋江採花》的某些情節和主題。05年,潘惠森跟獨立電影導演莫耀華合作,構思動畫電影版《武松日記》,現在的劇場版則是按電影版本改編而成。
「語言」向來是潘惠森劇作中最突出的劇場元素。他偏好港式廣東話的語感,對白韌力強,但角色之間的對話往往互不搭腔,因而形成一種幽默中暗藏荒謬的語言狀態,劇中角色即使缺乏傳統意義下的戲劇行動,語言的韌性仍能營造出別開生面的戲劇性。這個特點在潘惠森早年的「昆蟲系列」和「珠三角系列」作品中尤為鮮明,構成了香港戲劇中無可忽視的風格板塊。近年潘惠森有返璞歸真之勢,在10年前後的「人間系列」裡,雕琢語言的痕跡已沒那麼棱角分明,再加上對照潘惠森一些「系列外」劇作,像《親愛的,胡雪巖》、《都是龍袍惹的禍》等歷史劇作,晚近的潘惠森再沒有早年那種實驗色彩,反而多了一份在戲劇上的世故、圓熟和透徹。
在《武松日記》裡,我們仍可看到不少潘惠森式的語言雙打,但更值得觀眾細味的,反而是他在多年後怎樣再以「水滸江湖」借喻其個人世界觀。潘惠森有著一股獨特的江湖味,不全是豪氣干雲,不全是腥風血雨;更獨特的,是那種在闖盪和退隱之間的搖擺不定,蒼涼而帶笑、欲哭又無淚,雖鬱悶填臆,亦似有所悟的唏噓情態,這的確與《水滸傳》的「退」意頗有共鳴之處。這種充滿江湖味的猶疑不決,在他早期作品裡通常被演繹為香港九七的身份焦慮,但到了《武松日記》,我們發現「文化認同」的社會維度不再是劇作最急切要表達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潘惠森與《水滸傳》裡這群江湖人物的對話─ 這或許才是一個劇作家最原初、最質樸的創作關懷。
《武松日記》是武松的故事,其中保留了《水滸傳》中家傳戶曉的「武松打虎」和「殺西門慶」等「武十回」情節。這些情節在劇中卻變得無足輕重,主要劇情反而放在武松上梁山後的落泊心境上,這恰恰是《水滸傳》裡一個被壓抑了的主題。劇中還有另一要角李逵─原形是潘惠森舊作《李逵的藍與黑》中那以當畫家為志願的李逵。《武松日記》中的李逵實現了他在《水滸傳》中的未竟之志,竟擅自入京行刺皇帝,而宋江為免妨礙招安大計,便派武松跟眾兄弟阻止。全劇就是在這條脈絡裡展開故事。但潘惠森顯然無意細緻刻劃這場江湖戲碼,劇情推展很快,快得甚至有點兒戲、有些可笑,卻反襯出武松唏噓心境。劇中李逵渾號「戇逵」,但心中比誰都雪亮,他一心以畫家為志業,上京行刺不過是幌子,真正目的其實是要「尋夢」─一種退出江湖的手段。對武松來說,李逵正好是他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他想做而不敢做的理想形象。
武松以「打虎」聞名天下,但《武松日記》的「虎」卻是一隻看透世情的「貓」。在跟貓的漫長對話中,武松似有所悟,漸漸明白到江湖上的一切名望功業,原來不過是虛名,人生在世,都是身不由己,最終竟不及一個放棄畢生事業、義無反顧地去做燒餅的掌櫃。「做燒餅」本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的職業,在世人眼中─ 或說在《水滸傳》世界裡的世俗視野裡─ 武大郎跟武松是兩個檔次的人,武大郎醜賤而武松俊猛,人人都讚賞武松而鄙夷大郎。怎料事到後來,武松竟放棄豪情壯志,返璞歸真回去學做燒餅,這跟「戇逵」作畫互相呼應。至此《水滸傳》裡沒有明言的一個「退」字,終於得以發揮,亦發揮得相當愜意。
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術業。有道是:術業有專攻。執於一藝雖仍是執著,卻是對世情俗事的大放下。潘惠森的劇作家生涯一路走來,難道不也有此等轉念嗎?劇中的武松和李逵,小執著而大放下,隱然又是潘惠森的寫照。《武松日記》起源於他的日記體「偽小說」,如今劇中也保留了日記體的敘事形式,並借鴇母、春花和秋月三個風麈女子之口說出,如旁白一樣穿梭於全劇的情節推展裡。「春花」、「秋月」之名,典出李煜名詞〈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為武松故事更多添一份看破世情的唏噓。但這唏噓是帶笑的,是幽默,也有種港式「麻甩」味。這當然來自潘惠森獨步香港的戲劇語感,然而比起年輕時的潘惠森,現在的他寫得更鬆更闊,沒有「昆蟲系列」中那些緊湊逼迫的節奏和劍拔弩張的對峙,反而流露著一種世故的淺白。這就好像武松不再勇武打虎,而是專心一致,做一塊簡單中見真灼的燒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