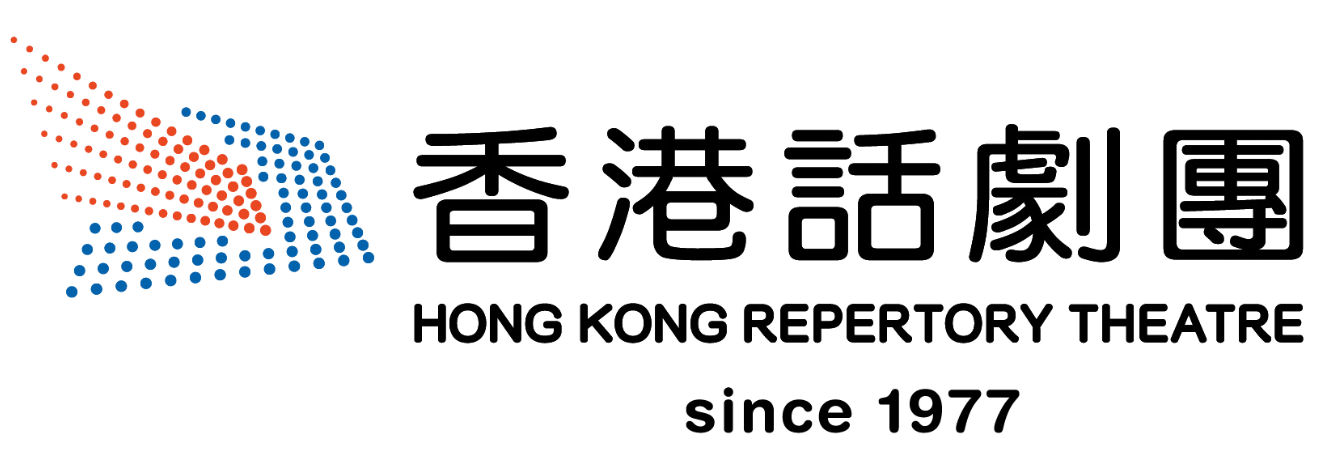戲劇文學
講史者的情懷— 評《親愛的,胡雪巖》
《親愛的,胡雪巖》是潘惠森先生十多年前所寫的一齣歷史故事劇。若不太嚴格的話,也可算是瑞士德語戲劇家狄倫馬特(F. Dürrenmatt)所說的「非歷史的歷史劇」。劇中的主人公─胡雪巖,史有其人。姓胡,名光墉,字雪巖,先後歷經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白手起家,辦錢莊,開藥鋪,倒生絲,販軍火,上通官府,下通漕幫,出入租界、洋行,廁身歌場、妓院,層層托靠,左右逢源,官居二品,富甲天下,又納粟助賑,施藥救病,一時傳為佳話。然而關於胡雪巖可採信的歷史記載,少之又少,如今坊間廣為流傳的其人其事,多屬稗官野史的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的賈語村言。如此說來,這類作品的出虛入實、編織有無,其優長與否,便不在作者鉤沉抉隱、索幽發微的學問工夫,不在治史的博見與精識,而在講史者的情懷,在於一個好看好玩的歷史故事背後所負載的文化旨趣與當代意識。
作為一個講故事的行家裡手,在《親愛的,胡雪巖》中,潘惠森不為觀眾提供人物行為的歷史解釋,甚至連戲劇事件的前因後果也作了大膽的省略。人們不明白一個窮得衣食不周,僅能以鹹豆佐餐的錢莊小夥計,從何處弄來五百兩錢的銀票,去資助一個非親非故的落魄書生;不明白掌控著海運、河運大權的官府,為何要與下九流的漕幫混在一起⋯⋯晚清政局的亂象,統治集團內部對外夷「剿」與「撫」的對立紛爭,官商政治現實關係的複雜性,太平天國之亂⋯⋯統統蜻蜓點水般被推至後景。劇作的重心,主要放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性格、神采與命運上。「這一個」胡雪巖之所以可親可愛,不僅在於他慷慨資助王有齡,收留賴老四,結交龐天,知人善任,樂善好施,賈而近儒;更在於他那「要開全世界最大的銀行」、「啲洋人嚟中國,唔係搶錢,係同我借錢」及「我要中國嘅老百姓食得好、著得好、住得好」的愛國情懷與歷史抱負。一個對自己的人格價值充滿著深刻自覺的胡雪巖形象,正是他區別於以往那些「君子富,好行其德」(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的富商巨賈的不同之處。
這裡所涉及的,不是傳統社會童叟無欺、薄利多銷、人棄我取、不為己甚的理財文化與商業倫理,而是一種超越性的、嶄新的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談及這類新型商人獨特的精神面貌,及其手段與目的的悖論。他說這類商人一生以賺錢為「天職」。不過他們賺錢,既不是為了個人的享樂,也不是為了滿足任何其他世俗的願望,無休止地以錢生錢,其精神是「超越而又絕對非理性的」。所謂「超越」,也即是超越俗性的神性維度。充滿悖論的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人必須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來實現這一非理性的目的。
在《親愛的,胡雪巖》的情節推展中,有兩處彷彿有意偏離情節軌道的談論黑洞的段落和一處別具深意的「祭鹿儀式」,正是作者特意安排的超現實場面。胡雪巖在孤注一擲地壟斷茶葉市場、逼迫洋商就範的關鍵時刻,一個人獨自站在茶葉箱已被搬走、顯得格外空蕩和幽暗的貨倉裡,忽然一位猶如先知的青年女子─ 船姑阿香,同他聊起吞噬一切的黑洞。廿三年後,老年的胡雪巖如法炮製,在另一場與洋商的殊死搏鬥(壟斷生絲市場)的節骨眼上,他對阿香姑娘說:「我就係個黑洞」、「個黑洞就係我自己。」在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正式啟業的祭鹿儀式上[1],在扮演「鹿人」者與操刀人近乎狂迷的祭舞神樂中,胡雪巖忽然站起身,神情恍惚地覺得自己就是那頭「鹿」,那頭在祭神儀式中被獻祭的犧牲。他感覺到操刀人插向「鹿人」的刀,彷彿刺向自己的身體。隨後他對國藥號的經理麥錦秋說:「我成日都覺得,十二生肖裡面,冇一樣嘢係屬於我嘅,因為我一生出嚟就係一隻鹿⋯⋯佢嘅本能就係,走出森林,邊度有廣闊嘅原野,佢就去邊度,永無休止⋯⋯好似喺一個黑洞裡面奔跑,永遠見唔到盡頭⋯⋯」「黑洞」是一種透過天文觀測才能見到的天象,它指恒星死亡過程所產生的具有極強引力的內壓坍縮。在劇中,「黑洞」被移用來隱喻某種推動胡雪巖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超現實力量,既顯露主人公人在漩渦、身不由己的忐忑不安,也呈現冥冥之中莫測高深的玄秘。
在戲劇中,超現實場景是一種夢幻與現實相互滲透、相互交纏的藝術化現象。它給導演藝術家提出巨大的挑戰,也為舞台呈現留下廣闊的自由空間。《親愛的,胡雪巖》的戲劇故事本身,就帶有濃重的傳奇色彩,導演的難點,不在刻意營構非寫實的奇觀異景,而在追尋懸浮在敬畏與迷濛的戲劇氛圍與審美情調上空的精神層面。
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道路異常艱難。鴉片戰爭之前,朝野幾乎都沒有自覺地考慮過如何使國家近代化,因此,中國現代化任務中還包含著大量尚未完成的近代化課題。對潘惠森來說,在舞台上思索現代如何展開的課題,或許太過沉重。因此他選擇一個出虛入實的傳奇故事,將中國現代歷史的前奏,置於一個半神化的、超常的歷史現場。作品最為成功之處,不在仔細描摹胡雪巖在生意場上愈戰愈勇、春風得意的情狀,而在表現他生命史中每每省悟獨負歷史重任的自覺,在現實場景與超現實場景所形成的巨大張力。然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不知是歷史事象迷霧重重,還是作家曲筆婉轉,歷史的陰差陽錯比作家的情懷更嚴酷。在劇中,已升任浙江巡撫的王有齡回天無力,在太平軍攻陷杭州城後吞金自縊;調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在胡雪巖的心靈感應中,悲歎「呢個國家⋯⋯已經唔再需要我⋯⋯生來兩手空空,死去兩袖清風」頹然倒下;一場壟斷生絲市場的對決,內奸外敵相勾結,全國三十幾間阜康錢莊,同一時間發生擠兌,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不是轟然倒塌,而是噗哧一聲全部沉陷,只剩下一塊聊作補船之用的藥店橫匾⋯⋯潘惠森如此費盡心力地形塑一個完美的理想人格,想像或假設歷史的另一種可能,吊詭的是,他最終呈現的是這種「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的不可能。
人們總是依據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期望,來講述自己的現狀。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B. Croce)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歷史學的生命力,不在對歷史資料的羅列與梳耙,而在於歷史的當代性,在於對當代現實的關照與精神聯接。歷史劇、歷史故事劇,不僅僅是編導者、演出者對歷史的虛構,也是一代代人對歷史的期望,一代代戲劇藝術家的歷史情懷。我相信觀眾所看重的,絕不是隱藏在戲劇場景後面的歷史真相,而是戲劇所呈現的人對歷史的承擔。無論是不可承受的輕,還是難以承受的重,總有一類人,註定要自覺地背負歷史的重任。正因為有他們的存在,喜劇也好,悲劇也罷,歷史的活劇才不至於只剩下淚水與血污。
[1] 在2018新版的演出中,導演為祭鹿場景另有處理。
[1] 在2018新版的演出中,導演為祭鹿場景另有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