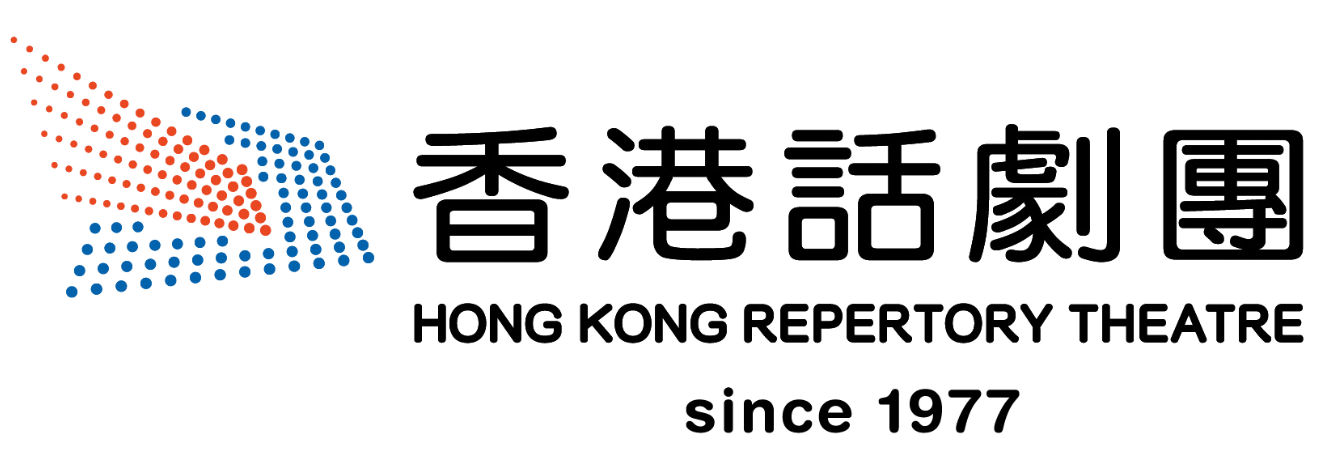戲劇文學
《結婚》的時代意義
香港觀眾認識橋田壽賀子,離不開《阿信的故事》。《結婚》原是1982年的電視劇本,乃TBS電視台星期三劇場的作品;翌年改編成為舞台劇公演,1984年便翻譯成中文,且曾在內地公演。《阿信的故事》由83年播放至84年,兩者的時代背景可謂相同。
1983年也是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的開幕年份,此所以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壓根兒找不到任何理由在普天同慶的日子中,去看一部詳述昭和年代悲慘歲月的NHK電視劇。大家均沉醉於歌舞昇平的氣氛,急著要趕上時代的步伐,希望成為急行列車上的一分子,分享日本經濟全面起飛的成果,成為得勝者的一方。《結婚》中沒有明確交代花田家身處的時代背景1 ,但母親與四姊妹相依為命的故事,明顯流露出經濟匱乏胼手胝足的艱難歲月日子紛擾。八十年代日本正值泡沫經濟期,社會上正處於紙醉金迷的狂歡雀躍年代後,《結婚》所刻劃的世界更加好像與發表時空的社會情狀有一定距離。
匱乏的鍾情
橋田對時空設定中的經濟匱乏背景從來有所偏好。宇佐美保在《橋田壽賀子和戰爭及巴爾裁判官》一文中(巴爾即Radhabinod Pal,即二戰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裁判官,他是當年唯一認為日本所有戰犯無罪的裁判官),指出橋田一直以身為「軍國少女」而自詡。事實上,橋田的而且確有參與日本二戰,曾於陸軍省負責暗號密碼的翻譯工作,後來投身於海軍部。橋田回省個人的戰爭經歷時,直言「戰爭與和平」乃自己寫作的一大重要主題。她認為在戰爭年代中,某程度有它幸福的一面。因為所有人均處於物質匱乏的狀態,所以大家都得以寬大為懷,僅以爭取戰勝作唯一目標。反觀今天的世界又如何?即使手上拿著名牌物品,但旁人身上更名貴的東西早已令人心生憾恨。所以她所指的身處戰爭中的幸福,乃指大家條件一致均化,於是不幸也不存在。
明白橋田的思路及價值取向後,相信對理解她劇作中的人物及背景設定,便可更清晰透徹。此所以成於八十年代的劇本《結婚》,花田家的經濟匱乏於橋田的世界中是必須的,因為所代表的是一種人性共融同感互滲的基石;唯其一無所有,彼此必須守望相助 才可以渡過難關。反映於劇作中即老媽的工作不休,甚至還沒退休已在張羅未來兼職之事;秋子為妹妹拚命工作;冬子則輟學持家支援所有成員。凡此種種的設定,正是橋田強調人性光輝的切入點,正如《阿信》透過山形的苦寒及經歷的坎坷來成就阿信的偉大,恰好屬大同小異的精神脈絡安排。
女性的自主覺醒?
自八十年代開始,日本的女性主義思潮便開始逐步萌芽,但現實中的日本女性只能意識到男女應要平權,卻從來沒有真正體驗到獨立起來的社會變化,簡言之也未能從女權解放的思潮中得到甚麼具體的得益。母親花田花所身處的自屬男性當道的世代,而能夠自主人生命運的空間,就 只剩下退休後的老年生活─一個屬於可以由個人自主自決的黃昏領域。文本中由花田花對婚姻持有負面想法,到劇終前決定與友鄰太助重訂姻緣,成為「熟年婚姻」的一分子,當中的心理變化及行為轉向正是橋田壽賀子希望為角色注入女性解放追求自主的時代元素。
大姊秋子正是剛才提及體會到男女平權的新趨勢,可是現實上卻全無獲益的一分子,劇本中抱怨被後來者又或是男性在職場上不斷爬頭爭先,正是明顯的例證;再加上因為家庭負擔,於是連談戀愛的衝動也壓抑下去,成為四姊妹中最可憐的一人。冬子選擇從學業中退下來,成為專職打理家務的一人。夏子學歷最高,將有機會成為醫生,卻選擇放棄考試而出嫁法國開展新生。么女春子更在求學期懷孕,且決定與正吉成家立室,胼手胝足去迎接小家庭的刻苦人生。以上五例,不是在職場上失意,就是自決逃避職場的人生選擇,改以家庭為未來目標,擁抱婚姻的價值。
橋田劇本中的女性覺醒,不約而同以婚姻為終極取向,可是這也正是我們值得思考的要點─是否一定要找到順心稱意的一半,那麼結婚的價值才得以成立?結婚作為女性獨立自決的體現,是否有預設的先決條件?如果有的話,那還可以稱得上為自決嗎 (受制於外在條件左右)?如果沒有的話,為何四人的成婚條件前提又趨向同一?
[1] 是次演出版本的時代背景設定為八十年代。
湯禎兆
香港作家,專攻日本文化研究,出版著作大多有中國簡體、台灣繁體及香港繁體等不同版本。近著有《亂世張瞳》(香港生活書房)、《人間開眼》(中國三聯)及《悶騷日本》(台灣奇異果)。2013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組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