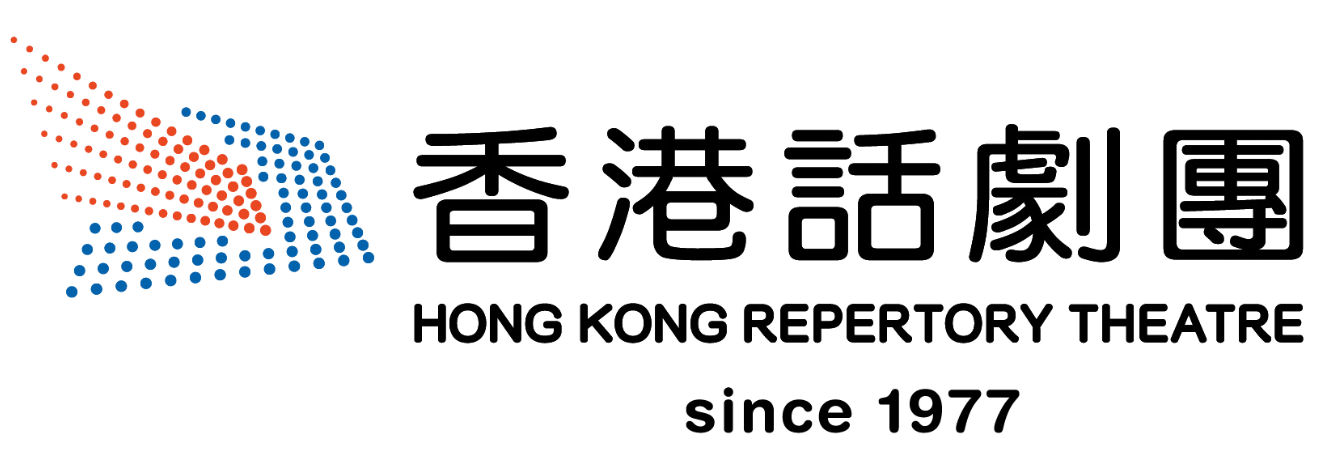戲劇文學
夢裡夢外 ─《如夢之夢》導賞
儀式與故事
進入劇場,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來。不久戲開始 了,觀眾就給演員包圍著,他們順時針繞圈。繞圈, 從 此在劇場內不間斷地進行。這個往前行進的動 作,一開始便是個集體行為。或快或慢,連續不斷,帶著東西的,不帶著甚麼的,明顯地帶著某些情緒 的,看來似乎比較漠然而無所謂的⋯⋯慢慢地這個 繞圈已經不單是一個劇場內的「行為」了,它是個有 意為之的劇場符號,它是一個儀式。然後,你會發覺,這個戲的儀式可多呢!「點蠟燭」 就是一個。醫生想聽五號病人的故事,病人要她帶 支蠟燭來。先要點起蠟燭,故事才可以開始。唯有 儀式,才顯出故事的莊重性。你購票看這個戲,要 經過到票房排隊、付錢,到時候要預算時間換衣服 出門趕交通步過一段路程等等程序,你若把這些視 為「儀式」,這個戲也許會更顯分量。「儀式」通常 有它的傳承關係。「點蠟燭」就貫徹首尾,到第二部 分顧香蘭講故事。蠟燭、古董燭台⋯⋯你恍然大悟:五號病人的做法應該是從顧香蘭處來;顧香蘭呢,也自有她建立這個儀式的來處⋯⋯
於是,光是從儀式著眼,你也看到趣味,看到美。
「埋東西」也是儀式。今天我們叫「時間囊」的埋 東西,在戲中也一再出現。是情節,也是儀式。這儀 式在戲裡由江紅開始,她在土地以至地板埋下這個 或那個東西,給未來某個時間的某個人發掘出來, 從而發現出特別的意義。這,也是一個,讓人珍重的,儀式。
擴而大之,生活上的起居日用也可以賦予「儀式」的意義和分量。我們從外面回到家會脫外衣,從家裡外出會穿衣。但是,假如本來要穿上的外衣給人拿走呢?又假如遠行時要脫去外衣,讓身體變得乾乾淨淨呢?那都代表甚麼意思?
當然最重要的儀式還是環形劇場的佈局,和與之配合的持續繞圈而行。它有宗教意味,在印度以至西藏,信眾順時針繞行敲鐘禮敬;在一般中國寺廟,拜謁主尊之後,我們會順時針瞻 敬側面和背後的菩薩。繞行也有哲學意味。這呼應著東方的時間觀 念,春夏秋冬,生長收藏。萬物復蘇,生生不息。繞行讓一切回到原點。戲裡自然有直線元素,例如火車,尤其是在第二部分顧香蘭的故事裡。是近代的 火車改變了時間觀念,因天時而各處不同的時間, 卻因著火車而必須準確與歸一。而直線而行、通往未知的時間,也似乎根本改變了人的命運,包括顧香蘭的命運。但是,直線到底只是局部,包圍著直線的是個更大的圓。就如任何朝前飛馳的火車都離不開地球,最後,都回到原點。
諦聽死亡
回到原點的,本來就是生命。對很多人來說,生命在醫院開始,最後,也在醫院結束。
這齣戲是在醫院開始的。戲的第一個說故事者是醫生── 一位剛畢業、馬上要投入理想專業的醫生。可是 她沒有足夠心理 準備,迎接她的是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第一天上班,她當值的病房便連續死了四個病人。
我們「旁觀他人的痛苦」,應該怎麼辦?這是個當代眾所關心的問題。這個戲的年輕醫生首先是困惑、 無助、沮喪、挫敗,然後,她願意努力去學習幫助瀕臨死亡的病人。「自他交換」也好,「聽他說故事」也好,其實都是要接近以至進入瀕死者的生命。
拒絕旁觀,諦聽死亡。這是推動整個戲進行的力量。
點起蠟燭,它的光劃出了說與聽的空間。熒熒晃動的那一點燭火,恍似微弱然而真實的生命。這小小的一點燭火,本就是「主」字的第一筆。宗教與政治都取這個字去稱呼最有力者。面對燭火,我們會莊嚴地思考生命是甚麼,我們會卸去裝飾,撥去冗餘,珍惜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再沒有任何時候讓人更懂得「主」和「從」的關係了,回歸本源,就一如 《莊子‧養生主》中這「主」字的意思。這時,述說故事者認真地整理他的生命,諦聽故事者仔細感受別人的生命。這個從死亡而來的新的關係裡,有智慧,有美。
《 莊子‧養生主 》篇以「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結束,強調薪傳不盡的關係。或許正可以和這個戲相呼應。我們在演出過程會遇上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有預計中的,也有猝然而來的交通失事、高處墮下或心臟病發,不一而足。而最集中表現死亡的無可預計,是五號病人在說他故事前的「外一章」:西藏遊牧夫妻的故事。新婚的牧羊人在幸福的狀態下無端地失去愛妻,卻在陌生地方得到個剛失去丈夫的女人做妻子,然後又在最幸福的情況下突然失去一切。但原來這都只是一場夢。兜兜轉轉,甚麼得與失都不過是虛幻,牧羊人穿過死亡回到原點。似乎真實不過的生生死死,到底只是個夢。
余光中說:「一盞燈,推得開幾尺的渾沌?」(《守夜人》) 劇場裡的熒熒燭火,會給我們光照出幾多生命的執著與愚蒙?
夢與真實
我們都有夢的經驗。我們有時會想:今天晚上或許也會發個夢吧?但是,我們不可能預計這或會發的是個怎樣的夢。觀眾進場之前,都知道將會看到一個關於「夢」的故事。戲就叫《如夢之夢》。不是「如夢」之人生之風景之境界。第二個「夢」字強調這「夢」不是喻體而根本就是本體。說「如夢人生 」還認定有個「人 生」在,而賴聲川說:「如夢的終究還是個夢,只是你不曉得它是『夢』罷了。」
都只是個夢,夢始終會醒。繞圓而行的都會回到原點。我們大概都會預計,一如那位西藏牧羊人的妻子,戲裡面的失踨者死亡者,最後,或許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回來。不是有人這樣說嗎:人死之前,一生種種都會以最快的速度閃回來。
失蹤的回來了。埋下的給發掘出來。五號病人的妻子、江紅、王德寶、伯爵。又或者,這些人只是以另一個身分,出現在另一個人的另一形態面前?
或許都是另一形態。正如折磨、痛苦,換過另一形態,它或者竟是 快樂、璀璨呢?同樣的,快樂、璀璨,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是折磨、痛苦。江紅在戲 裡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最愛的東西給我們最大的快樂,也給我們最大的痛苦?」這問題不容易答。我們只能安靜下來,用心去整理,去諦聽,我們或許會有新發現。
夢中的痛苦不會是真實的痛苦。
經驗
看這個戲當然是難得的劇場經驗。觀眾要一直轉動自己的椅子,去尋找要看的東西,看這個複雜而簡單的故事。這個戲真複雜。故事中有故事。夢中有夢。一層又一層的,好像俄羅斯套娃,也好像易卜生晚年的《培爾金特》(Peer Gynt),戲中主角坐下來剝洋蔥,一層又一層的剝下來,直至最後。
不過,這個戲其實也挺簡單。生老病死、愛情波瀾、避難海外長期流放,以至妓女遇上過分投入的男人⋯⋯獨特框架裡的故事其實都不新鮮,而且,說故事者如五號病人、妻子和顧香蘭等,在說自己故事之先,都來一個「外一章」,並與一開首集體說的莊如夢故事相應,都是一把一把開啟這個戲的鑰匙呢!
藉著種種儀式構成的框架,我們可以用七個多小時,耐心地跨越情節,自然而然地、不自覺地以正常的呼吸進入他人的故事,去經驗他人的生命。這也算是「自他交換」的一種方式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經驗使「自己」成為「他人」。
這是《如夢之夢》在香港的第二次演出。它重臨舊地去尋找新的生命,就像一次旅行。戲、人生,以至夢,都是一回不確定的旅行。江紅離開中國之後不知道以後會怎樣,顧香蘭決定到法國也不敢設想未來,發著燒出發的五號病人當然也一樣。生命本來如此。人生一直在正常軌道上走的醫生,因為第一天上班馬上碰到四個病人死亡而感到挫敗,這才始了探問,才開展了這一個叩問生命的旅程。
旅行不是旅遊,你沒有得到甚麼「喪拼」戰利品,你只是獲得獨特的旅人經驗。同樣的,你這次不是「看了」一齣劇場經典,甚至不是「看了」一齣戲。你是「經驗了」一次獨特的劇場之旅,它關於心靈,關於你自己。
誰是這個戲的真正主角?誰最後能夠「看見自己」?江紅?顧香蘭?五號病人?醫生?或許是,或許都不是。這是個顛覆 劇場習慣的演出,佔據中央場 (centre stage) 的,是作為觀眾的你。
張秉權
戲劇藝術、藝術評論與藝術教育工作者、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