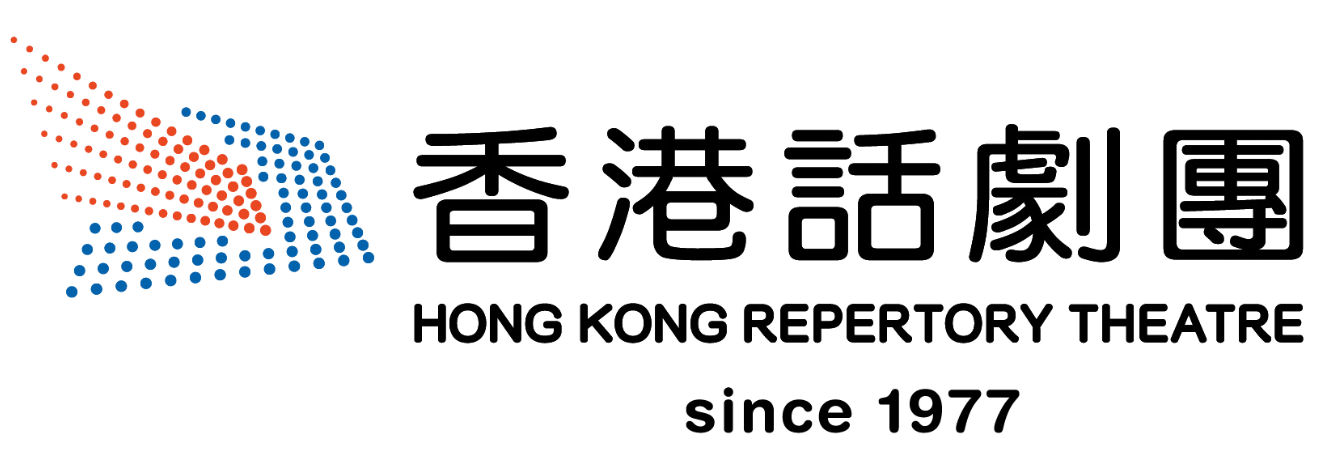戲劇文學
《叛侶》:對話,無止境的隔閡
對話失效産生撕裂
在對話失效的時勢看《叛侶》,我特別關注到當中的語言失效,人與人之間變得廢話連篇,沒有一句是為了與對方溝通而發的吊詭。說話沒有起任何作用,情侶如是,香港如是,社會現實如是。背景不重要,結局不重要,是誰扮演誰不重要。自殺是幌子,失蹤也不是重點,愛情倒真的變得無色無味無形無效。而關係呢?正中要害的,是與人同在時仍然隱隱約約的那份疏離感,愈接近卻愈遠離真相,愈有陌生感;愈渴求親密,愈崩離割裂。
愛是甚麼?這千萬年以來人類皆未能回答的提問,這齣舞台劇呈現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無愛偏要戀」的狀態,任何關係沒有保證、沒有延伸、沒有盼望,會是怎樣?一隻鞋、三部分的戲、五對情人,本來沒有多大關聯的,像蝴蝶效應,一旦對話發生了,就被 牽扯入莫名的溝通艱難的漩渦裡。一隻高跟鞋,一隻靴;一封信,一通電話 ─ 前者象徵行走、離開,後者象徵溝通、連接。事不關己,卻不斷討論;事既關己,言猶在耳,卻置若罔聞。錯置的時空,失去的關係,出走的情人─整個劇場,彷彿沒有太具體的行動,沒有高潮,但處處都是張力矛盾,彷彿翻揭很多未能解決的問題,又彷彿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問題。很多問題,似乎無疾而終。
彼此背叛又探摸
從一開始,編劇像上帝,締造這場矛盾,把觀眾置身事外,又彷彿比當事人知道得更多,但這也是觀眾心理期待最痛苦的所在。兩對「偷食」的夫婦於同一晚發生一夜情(其中一對最終懸崖勒馬,可是心理上早已出軌)。他們的對白彼此似在呼應、暗示、回答、質詢自己,觀眾或許會產生幻覺,他們在不同空間,在向對面那正出軌的伴侶質詢。夫婦之後在一起時,又在彼此探摸與閃躲中,出現了類似的通感和應。再而兩男、兩女無意中相遇,在建立一種幾乎貼近交淺言深的狀態,卻摸底揭露了對方曾與自己伴侶有一手,這是何等的頹唐。
觀眾又再一次成為最知情的旁觀者,也同樣是受騙者,因為編劇似乎沒有準備讓觀眾移情投入。大量戲劇對白,表面上跟對手講話,同時又有點像夢囈般的自言自語,彷彿是向觀眾敍述自身的對白。可是由於有時角色是在講述自己的想法,或直覺反應,變相有些部分出現類似對位敍述(counterpoint narration)的情況,像有一種說法,利用人物的想法拉開劇情,拉遠焦點,明明現實是衝突失望,卻把它搬弄成笑位和錯覺的調劑。第三部分,心理醫生Valerie的丈夫,是她輔導對象的現任情人。一段三角關係,通過輔導場景和電話留言的交疊呈現,這種近似對位敍述更為明顯,自然地淘汰了輔導室場景裡的嚴謹和專業,觀眾到底要相信誰?這種對角色的嘲弄,對觀眾心理期待扭轉的方法,抵銷了本來不真實的巧合和機遇。導演要求演員用怎樣的風格演繹對白,亦是十分關鍵。看過一些外國劇團演繹,有些色慾場面,舉手投足,大鳴大放;有些則把人物行動收斂,對話成為主要的內在行動,這便是挑戰演員的戲劇感和內在力量的時候。導演在處理時,又會否加插香港當下的背景?把英語對白翻譯成港式對白後,怎樣保留原文因語序所產生的敍述效果,而不至過於離地?這是對導演和演員的期待,也是這劇本為甚麼不斷吸引不同地域的劇團翻譯並演出的原因。
愛的表達不是一個口號
劇名翻譯成《叛侶》,背叛和情人的忠誠,相信就是這次演繹的指涉。愛裡必然包括信任,情侶太容易講愛,卻不講信任,愛和信任是伴侶的「倚天」「屠 龍」,缺一不可。我們不能只宣諸於口而沒有真情實感的愛。港人平日聽得太多大量政治宣言,人人都說愛香港,這種集結式、口號式的話語,經常缺乏質感。人釋出的話語像錄音機,沒有調整機能,沒有接收能量,行為上卻是不斷的傷害,愛,便無法令人信任。
情緒智商的專家常常鼓勵人表達感受、表達愛。前提是,我們先要切切實實懂得自己感受。劇中人忖度情人的愛,懷疑自己愛的分量,或愛本身可以堅持多久,說穿了,是懷疑自己。人類的感受細密和幽微,有時混濁,有時清空,更多時是錯綜複雜。自己也難於對自己的愛描畫清楚,更何況用說話釐清?文學、戲劇的功能(雖然藝術是超功能的,不以功利為本相)也包含這種細膩的捉摸。愛不是從對話發生,亦因為這種難以發生的無色無味,信任更是無法輕易抓緊。所以澳洲導演Ray Lawrence改拍成電影 Lantana,中文譯名是《愛情無色無味》就是這個意思。
劇中第二部分是嚴重的溝通迷障。每個角色把自己的情感或事情的來龍去脈塞給對方或者觀眾,但任何一方的呼求從未被回應。在他們每個人口中的敍述,都可以是一場場戲劇性行動,但編劇要求演員把戲劇性行動講出來,而不是演出來,這種失敗的溝通,表面上交代劇情或背景,但實際上更加強了吊詭和懸念,這種把對話雙方的思緒、掙扎加疊摻和的情況,理性對話額外顯得荒謬。社會很多標榜所謂理性對話,但在多元的社會裡,理性往往變成否定情緒反應,為情感區域劃界線的藉口。缺乏同理心和情感的介入,細緻敏銳的情緒不受尊重,造成更多溝通的障礙。觀眾多少會從這齣劇體會到,愛和信任、背叛和罪,不能用理性來闡釋。正如觀賞此劇時,完全理性根本不可能;觀眾必須想像,對白背後,角色對自己所劃的思想界限,他所說的,他也不曉得。
對白演繹內在心理行為
劇名Speaking in Tongues對我來說,自然聯想到聖經裡的方言。方言的產生來自人類的驕傲,野心建設巴別塔(Tower of Babel),自比天高,與上帝同等。結果上帝改變了人類口音,以方言使人類的溝通再不是必然,必須經過學習。方言的障礙又使人產生無止境的隔閡,直至我們承認個人不能頂替全知全 能的上帝。另一說法,方言是神賜給祂的信徒恩賜,是天使的話語,我們不知道方言在說甚麼,只知道使用方言祈禱便可直達天庭。這種神學理解與劇中人的悵惘有點共通,就是彼此言語不通,仿似自言自語也不知自己說甚麼,只有愛他的人才讀通方言。台灣劇壇曾把此劇譯成《言舌》─ 舌頭上的言語,誰最清楚?對話,你說變得何等神聖!聖經《雅各書》說,舌頭雖然是身體上一個小小的部分,卻能大大地自誇。像那麼小的火,能點燃那麼大的森林!這個劇名和這劇的手法,不知是否想勘探這座森林。
最後,為免劇透,我只能提醒,此劇以對話的內在心理為主線,觀眾必須學習預備直面幾項觀戲的挑戰:
第一、對白不時對觀眾情緒和判斷加強控制,誤導你誤判關係,這是另一種背叛本身。所以看任何戲,也不必盡信角色在講真相。對白是用來引導你進入, 或對抗某種狀態。現實如此,戲劇如是;
第二、對話既然不達至溝通的果效,必須承認對白的模糊性和虛假。這個敍述對白抑或戲劇對白難分辨的劇本,獨白也好,自言自語也好,對白的非合理性,倒更要期待演員把內心行為演出來,不是講出來。戲劇如此,現實更加如是。
這齣早在澳洲成名的劇作,會否對當下香港人心釋出某些善意的忠告,拭目以待。如果你已經不相信的話,你還有勇氣拿出信任,繼續面對自己,否決一切用對話包裝而拒絕介入情感關注的溝通嗎?雖然這是無關宏旨的。
吳美筠
澳洲雪梨大學哲學博士。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創會委員及現任董事、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創會主席。曾於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等院校任教。香港藝術發展局民選委員及文學委員會主席(2014-2016),現為該局藝術評論委任評審員。2018年香港教育大學駐校作家。出版文學作品多部,著有藝評集《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編《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創辦中學生雜誌《珍珠奶茶》,深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