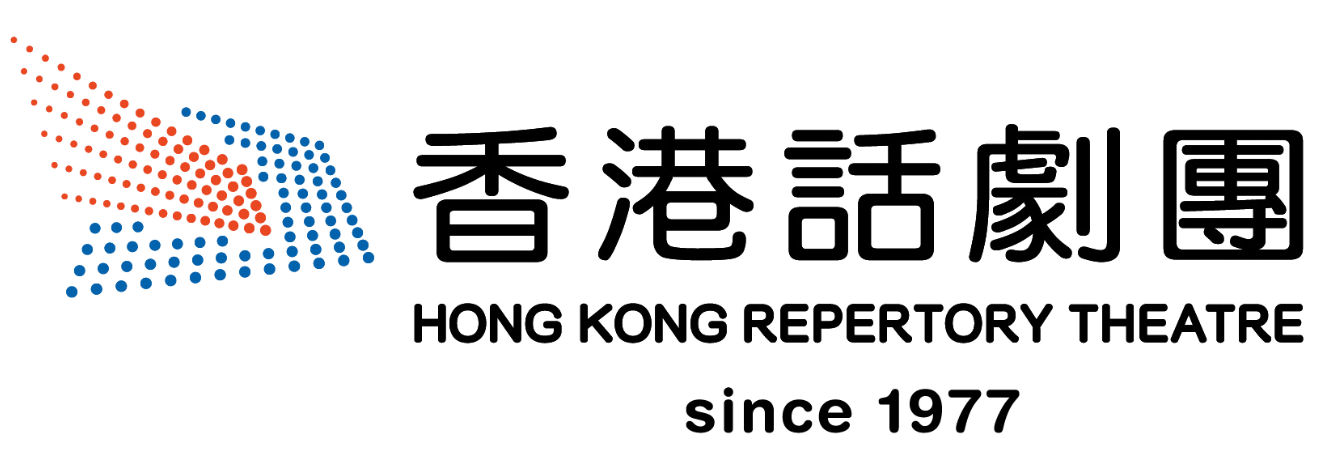戏剧文学
陌生的自我及其文化隐喻—对《往大马士革之路》的一种解读
1886年,奥古斯特.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传《一个女僕的儿子》(The Son of the Servant)。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认为,完整地描述一个人的一生要比完整地描述一个家庭真实和有启发得多……人们只瞭解一种人生,他自己的……」随后,他又接连出版了《一个愚人的自白》(The Confession of a Fool, 1893)、《地狱》(Inferno, 1897) 等书。据专家考证,这些着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为书中虽有大量真实的细节,却又夹杂着太多的想像、梦幻和编造……书中那位名叫史特林堡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混杂着真实和虚构的综合体;那个不断出现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既是牺牲品、又是救世主的「陌生人」,与传主不是同一个人。
史特林堡的主要剧作,从早期的《父亲》(The Father, 1887),中期的《往大马士革之路》三部曲 (To Damascus: Parts 1-3, 1898–1901)、《一齣梦的戏剧》(A Dream Play, 1901),到后期的《大路》(The Great Highway, 1909)……其主人公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如梦如幻,诡异荒忽,隐秘的心灵活动变成直观呈现的戏剧「场景」,纷纷沓沓,莫可穷诘。作为从传统戏剧挣脱出来的激进的先锋作品,作为传递新思潮、新观念的现代戏剧的起点,这些作品自有其内在的真实性和不朽的艺术价值。彼得.斯丛狄 (Peter Szondi) 在《现代戏剧理论》(Theory of the Modern Drama) 一书中,将这种戏剧样式称为「场景剧」(Stationendrama)。
「场景剧」一反传统戏剧、尤其是佳构剧环环紧扣的情节结构,不倚重因果关联的时空顺序,更没有由矛盾冲突所推动的连续性情节,而是由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所铺陈的一系列松散的戏剧场景所构成。场景剧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戏剧。它从中心人物的主观视角观察周围世界及其自身,描述中心人物内在(精神)的发展道路,揭示中心人物隐秘的心灵活动,以自我的统一取代情节的统一。
在《往大马士革之路》中,主人公陌生男,无名无姓,生活在超歷史时空中。他是该隐(Cain,额头有被刀斧砍伤的明显记号)[1];他是雅各(Jacob,走路一瘸一拐)[2];他是乞丐、是疯子、是凯撒……在他身上汇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特徵,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同的人的复合体。或者说,他是史特林堡心目中的人类的象徵。
陌生男忤时愤世,孤行独市,内心骚动不安,飘缭摇盪,从深度压抑到无端喜乐,情绪起伏不定,有如精神分裂症病患的极度敏感与狂热暴烈。一方面,他抱怨自己是一个被社会碾压与抛弃的人,一个多余人、局外人、陌生人;另一方面,又自视甚高,把自己看成是这个世界生存的最后救赎。
剧中出现的其他人:医生、乞丐、疯子、凯撒,甚至妇人……都可以说是陌生男这一中心人物的自我投射。然而,这些断裂成无数碎片的「自我」,也不再是陌生男所熟悉的「自我」。当外射的自我变成自我意识审视的他者时,已完全异化成某种让人难以辨识的东西。也就是说,陌生男在各个场景中遇到的人与事,包括医生、乞丐、疯子、凯撒、妇人……既是陌生男的自我,又不完全是陌生男的自我;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自我返回自身,从无意识的自我,变成意识到的自我,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一如彼得.斯丛狄所指出的,个体的自我与异化—对象化世界的对立,构成了史特林堡许多作品形式结构的基础。
在《地狱》一书中,史特林堡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开始寻找上帝,而我发现的却是魔鬼。」一方面,他从不停止痛斥现实的污垢与生存的错乱;一方面又不懈地唿喊要匡正这个脱节的世界。这从全剧的剧名、剧作结构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剧名中的「大马士革」,只有模煳不清的宗教意义。生活在别处,大马士革无论是象徵圣地或人间乐园,都虚悬在主人公的旅程之外。
陌生男千里投荒的流浪旅程(或心路歷程),从第一场的「大街转角」,回到最后一场的「大街转角」,兜了一大圈,终点回到起点,没有歷史,只有重复。
史特林堡一生遭受精神分裂症的多次困扰。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种伤害转化成深刻的人生体验与对世界的领悟,并在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以独到的场景剧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无论这种呈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背离精神分裂症的内在真实,也无论那种难以言明的神秘能否言说,它都帮助我们了悟艺术与生命所潜含的形而上学或宗教上的意义。
德国哲学家、精神病理专家卡尔.雅斯贝斯 (Karl Jaspers) 称史特林堡为「客观表现性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认为精神分裂症的病情发作,诱发了史特林堡原初人格中既有的艺术天赋。这涉及医学上更为精专的病理学问题。毫无疑问,并不是凡有艺术天赋的精神分裂症病患都能成为艺术家。我认为,在生存的挣扎与对抗,在对艺术的不断探索与追问中,敞开生存与人性的深渊,从而达到生命体验罕见的深度与另一个思维层次,或许才是史特林堡一类艺术家获得崇高艺术成就更重要的原因。
史特林堡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的作品或许可以被当作扭曲了的精神分裂症的艺术案例,而是在文化意义上,唤醒世人反省时代整体的精神处境,以及歷史目的化过程丧失给人类所带来的精神困境。雅斯贝斯将精神分裂症看成是西方现代文化颓败的隐喻。他说:「今天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找到答案:我们生活的根基已被动摇。时代问题敦促我们反省终极的问题与即刻体验。」(见《史特林堡与梵高》[3] 一书)事实上,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压迫,整体文化与生存处境正在经歷急剧的变化。变得陌生的不仅是客观世界,还有你自己。
西方如此,东方如此,香港亦如此。
[1] 编按:《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所生之子。该隐出于妒意杀了弟弟亚伯后,神在其额头作了记号。
[1] 编按:《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所生之子。该隐出于妒意杀了弟弟亚伯后,神在其额头作了记号。
[2] 编按:《圣经‧创世纪》中出现的人物。雅各与神摔跤时扭伤大腿,被改名为以色列。
[3] Strindberg and Van Gogh: an attempt of a pathographic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parallel cases of Swedenborg and Ho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