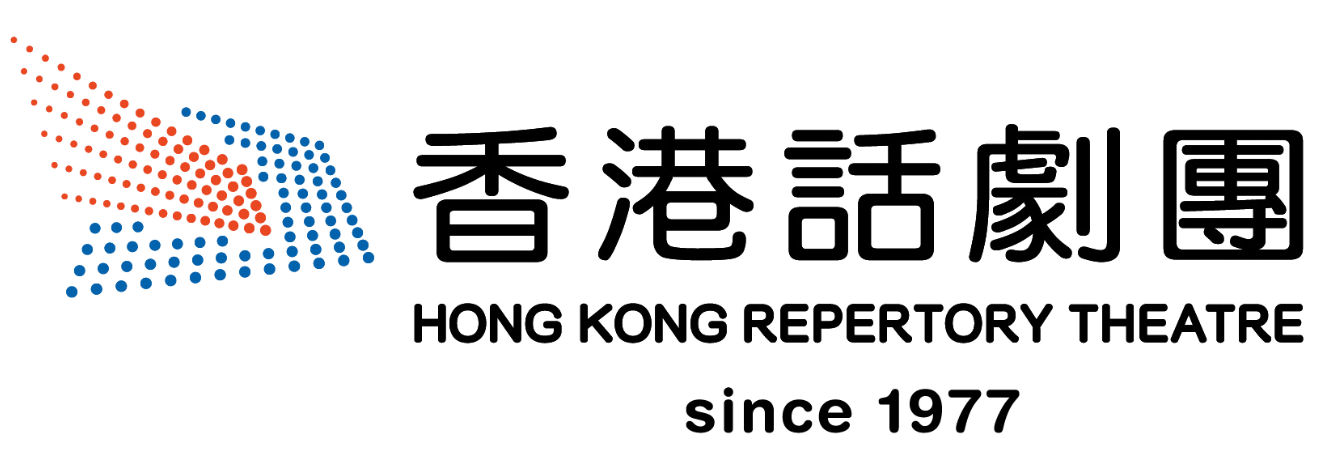戏剧文学
《 两刃相交》:现实作为一种 流,避无可避
台湾禅者林谷芳曾在其著作《禅 两刃相交》中,以剑客对决比喻参禅,意指禅的要义在于「看得透,且敢 于看透」,「必得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才能证生命的极致风光」。在书中还有另一句话── 「禅常以『何谓剑刃上事』提撕学人,要行者莫忘了,禅的存在永远直指那死生大事、根柢烦恼」。潘惠森的新作以「两刃相交」为剧名,不仅是看中其饱含的戏剧张力,更意在其蕴含的终极命题,即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直面某些「死生大事、根柢烦恼」。
故事发生在彭母百岁大寿这一天,彭家祖孙三代及儿孙的恋人们齐聚在酒店自助餐厅外的庭园,众人围绕着彭母这一核心角色,大致可分为三组:彭家三兄妹为一组;威武、端庄为一组;绰约、顶天为一组。而明显患有脑退化症、操着一口客家话的彭母,屡屡回忆起战争与逃难,哀叹衰老带来的生活难题,数记家人的名字与关系,更一直「做梦」──梦到自己轮流到孩子家中住,一直住到百年归老。
相较于过往作品,这还是潘惠森第一次如此大手笔地摄祖孙三代于一炉。通过剧中人的自白与演绎,剧作所涉及的时间广度长达一百年(彭家三代的百年流离),所触及的空间横贯香港与内地(后者以梦幻中开满莲花的池塘作喻),而所描绘的即是内地来港难民祖孙三代的故事。剧作者将彭家设定为「客家人」,我认为绝非偶然,值得注意。自西晋以降,因战乱、饥荒,中原人经历了五次大迁徙,至宋元战乱中,进入粤东并形成了客家民系。借由「客家人」这一特殊设定,「客」这一意象所指向的,是剧中人乃至香港人的某种生命处境,并在剧中外化为具体的命题。
剧作涉及养老、住房、时代变迁、代际沟通障碍,甚至生老病死与存在等具终极意义的命题,非常丰富和多样。事实上,这些命题有表里之分,形成了剧作的层次:彭家三兄妹为彭母养老问题而争论、高大寄居于前妻现任的房子、美丽将象征自由的金鱼煎给只懂得关心温饱问题的母亲吃,从此母女形同陌路──这些是具象的「表」;在表象之下,彭母的日薄西山、娇嫩的食道癌、端庄肚中即将出生的孩子、威武借艺术之名逃避女友怀孕,以及绰约沉溺虚拟游戏世界──这些是「里」,直指生老病死与人的存在问题,也即那些「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根柢烦恼」。
作为一名成熟的剧作家,我们可以看到潘惠森的野心,他所写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族群生存境况;他所描绘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题,且彼此之间无法交流。由此,无论是第一代内地来港难民的疑惑(对高速发展的城市与时代)与生存之难,还是难二代的困窘与矛盾丛生(温饱以上,精神以下),又或是第三代的决意虚无与自创生存哲学──通通冶于这酒店自助餐庭园的方圆之内,但所有人都无心进食。
当那「死生大事、根柢烦恼」来到剧中人面前,他们或逃避、或胡涂、或不知所措,尽显常人常态。「两刃相交」的时刻,并不那么容易到来,以至于现实成为一种潜流,而潜流之上的众生相,成为本剧的主体之一。
在现实之外,潘惠森的文本总是有着诸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两刃相交》中,无论是对调性别的表演设计、广播的运用,抑或是重重迭迭的繁复意象,都是剧中极为夺目的存在,更进一步让现实暂时隐身为一种潜流。
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在剧本开端就已作出说明的「所有女性角色由男演员扮演,男性角色由女演员扮演」。这一对调性别的表演设计,可见会为演出带来一种别样的滑稽与幽默感。但作为一个贯穿全剧的设计(创意),其功能绝非只有调笑,而是与美学观念和剧作表达息息相关:在美学观念方面,性别对调的表演类似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干旦坤生」,实质上破除了一种沉浸感,令演出呈现出「间离」的效果,这无疑是剧作者有意为之,试图让观众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而在剧作表达方面,由于此剧与「禅」关系密切,因此值得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在《维摩诘所说经》中,大乘佛教曾以「一切诸法……无有定相……非男非女」阐述其男女性别观,潘惠森刻意将男女调转,或许意在提示观众,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与根柢烦恼,从来与性别无关,而是众生之所共业。
剧中不时出现的餐厅经理广播,也提供了惊奇与间离效果。广播的功能颇多,但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是经理看似在提示剧中人自助餐的用餐时限,实际上却是提醒着观众演出的时限。这又可见剧作者的匠心。剧中的倒数不仅有生命倒计的意味,更让观众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终会完结的演出。
而那繁复的意象重重迭迭,有的浅显,有的意味深长,有的则梦幻至极、耐人寻味:莲藕饼疑似客家菜,是彭母的念想,是联想巨型莲花的关键道具,也是众人「关心」与「和解」的寄情物;自由开心的金鱼,是美丽与彭母两代人观念的裂痕,无关对错;得过小儿麻痹又被蜈蚣咬断三分之二翅膀的乌蝇,用剧中人的话说,是「魔咒」,象征着生命中的无常,同时也有「人不如乌蝇」的表达;会生癌症的家则隐喻家庭内部的嫌隙与紧张的关系;至于超现实的巨型莲花,以及目睹乌鸦救子、领悟高楼大厦像瀑布而「修成金身」的彭母,则是如此地梦幻、魔幻、耐人寻味──莲花自然与禅相关;彭母在目睹乌鸦救子之后,似乎也化成一只鸦,对着夜半突然出现的猫发出「呀,呀」的声音。在生命的尽头,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似乎有一种领悟,在电光火石之间闪现。在瀑布般的高楼大厦重重包围之中,家人与家庭或许就是一种无所躲闪的羁绊与联系。
当那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与根柢烦恼,因着剧中人的回避而成为一种潜流,剧作者又藉以上惊奇的设计和繁复的意象,进一步遮蔽了对现实的直接讨论——这恰是艺术的方式。但当这种间离效果愈趋频仍,观众自始至终都被引导着以一种清醒的状态观照剧中人的众生相,那么,现实作为一种潜流,就终归会重新浮现,并来到观众面前,触发反思。而此剧,无疑就是那现实潜流之上,开出的五光十色的花。
野获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舞台剧编剧、导演、剧评人,已公开发表剧评、剧本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部。
现实流之上的众生相
故事发生在彭母百岁大寿这一天,彭家祖孙三代及儿孙的恋人们齐聚在酒店自助餐厅外的庭园,众人围绕着彭母这一核心角色,大致可分为三组:彭家三兄妹为一组;威武、端庄为一组;绰约、顶天为一组。而明显患有脑退化症、操着一口客家话的彭母,屡屡回忆起战争与逃难,哀叹衰老带来的生活难题,数记家人的名字与关系,更一直「做梦」──梦到自己轮流到孩子家中住,一直住到百年归老。
相较于过往作品,这还是潘惠森第一次如此大手笔地摄祖孙三代于一炉。通过剧中人的自白与演绎,剧作所涉及的时间广度长达一百年(彭家三代的百年流离),所触及的空间横贯香港与内地(后者以梦幻中开满莲花的池塘作喻),而所描绘的即是内地来港难民祖孙三代的故事。剧作者将彭家设定为「客家人」,我认为绝非偶然,值得注意。自西晋以降,因战乱、饥荒,中原人经历了五次大迁徙,至宋元战乱中,进入粤东并形成了客家民系。借由「客家人」这一特殊设定,「客」这一意象所指向的,是剧中人乃至香港人的某种生命处境,并在剧中外化为具体的命题。
剧作涉及养老、住房、时代变迁、代际沟通障碍,甚至生老病死与存在等具终极意义的命题,非常丰富和多样。事实上,这些命题有表里之分,形成了剧作的层次:彭家三兄妹为彭母养老问题而争论、高大寄居于前妻现任的房子、美丽将象征自由的金鱼煎给只懂得关心温饱问题的母亲吃,从此母女形同陌路──这些是具象的「表」;在表象之下,彭母的日薄西山、娇嫩的食道癌、端庄肚中即将出生的孩子、威武借艺术之名逃避女友怀孕,以及绰约沉溺虚拟游戏世界──这些是「里」,直指生老病死与人的存在问题,也即那些「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根柢烦恼」。
作为一名成熟的剧作家,我们可以看到潘惠森的野心,他所写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族群生存境况;他所描绘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题,且彼此之间无法交流。由此,无论是第一代内地来港难民的疑惑(对高速发展的城市与时代)与生存之难,还是难二代的困窘与矛盾丛生(温饱以上,精神以下),又或是第三代的决意虚无与自创生存哲学──通通冶于这酒店自助餐庭园的方圆之内,但所有人都无心进食。
当那「死生大事、根柢烦恼」来到剧中人面前,他们或逃避、或胡涂、或不知所措,尽显常人常态。「两刃相交」的时刻,并不那么容易到来,以至于现实成为一种潜流,而潜流之上的众生相,成为本剧的主体之一。
现实流之上的惊奇与间离
在现实之外,潘惠森的文本总是有着诸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两刃相交》中,无论是对调性别的表演设计、广播的运用,抑或是重重迭迭的繁复意象,都是剧中极为夺目的存在,更进一步让现实暂时隐身为一种潜流。
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在剧本开端就已作出说明的「所有女性角色由男演员扮演,男性角色由女演员扮演」。这一对调性别的表演设计,可见会为演出带来一种别样的滑稽与幽默感。但作为一个贯穿全剧的设计(创意),其功能绝非只有调笑,而是与美学观念和剧作表达息息相关:在美学观念方面,性别对调的表演类似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干旦坤生」,实质上破除了一种沉浸感,令演出呈现出「间离」的效果,这无疑是剧作者有意为之,试图让观众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而在剧作表达方面,由于此剧与「禅」关系密切,因此值得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在《维摩诘所说经》中,大乘佛教曾以「一切诸法……无有定相……非男非女」阐述其男女性别观,潘惠森刻意将男女调转,或许意在提示观众,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与根柢烦恼,从来与性别无关,而是众生之所共业。
剧中不时出现的餐厅经理广播,也提供了惊奇与间离效果。广播的功能颇多,但最重要、也最值得关注的,是经理看似在提示剧中人自助餐的用餐时限,实际上却是提醒着观众演出的时限。这又可见剧作者的匠心。剧中的倒数不仅有生命倒计的意味,更让观众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终会完结的演出。
而那繁复的意象重重迭迭,有的浅显,有的意味深长,有的则梦幻至极、耐人寻味:莲藕饼疑似客家菜,是彭母的念想,是联想巨型莲花的关键道具,也是众人「关心」与「和解」的寄情物;自由开心的金鱼,是美丽与彭母两代人观念的裂痕,无关对错;得过小儿麻痹又被蜈蚣咬断三分之二翅膀的乌蝇,用剧中人的话说,是「魔咒」,象征着生命中的无常,同时也有「人不如乌蝇」的表达;会生癌症的家则隐喻家庭内部的嫌隙与紧张的关系;至于超现实的巨型莲花,以及目睹乌鸦救子、领悟高楼大厦像瀑布而「修成金身」的彭母,则是如此地梦幻、魔幻、耐人寻味──莲花自然与禅相关;彭母在目睹乌鸦救子之后,似乎也化成一只鸦,对着夜半突然出现的猫发出「呀,呀」的声音。在生命的尽头,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似乎有一种领悟,在电光火石之间闪现。在瀑布般的高楼大厦重重包围之中,家人与家庭或许就是一种无所躲闪的羁绊与联系。
当那无所闪躲的死生大事与根柢烦恼,因着剧中人的回避而成为一种潜流,剧作者又藉以上惊奇的设计和繁复的意象,进一步遮蔽了对现实的直接讨论——这恰是艺术的方式。但当这种间离效果愈趋频仍,观众自始至终都被引导着以一种清醒的状态观照剧中人的众生相,那么,现实作为一种潜流,就终归会重新浮现,并来到观众面前,触发反思。而此剧,无疑就是那现实潜流之上,开出的五光十色的花。
野获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舞台剧编剧、导演、剧评人,已公开发表剧评、剧本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部。